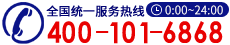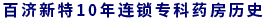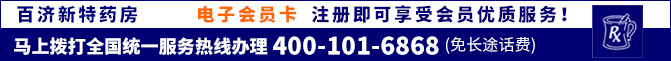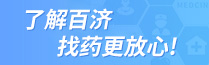您現在的位置: 百濟新特藥房網首頁 >> 消化系統 >> 腹瀉 >> 腹瀉治療研究進展
急性腦卒中并發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分析
- 來源: 百濟藥房藥訊 作者:百濟動態 瀏覽: 發布時間:2014/7/14 7:13:00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我院2003~2006年神經ICU住院的358例急性腦卒中患者,并且在住院期間均使用1~5種抗生素者為研究對象,其中急性腦梗死(CI)143例,腦出血(CH)121例,蛛網膜下腔出血(SAH)94例,男193例,女165例,年齡34~83歲,平均(66.8±9.7)歲。其中伴有基礎疾病(為糖尿病,高血壓病、心臟病、既往卒中史、腫瘤、慢性支氣管炎或風濕病)的腦卒中患者256例,伴有2種及以上基礎疾病172例。顱腦手術135例,為去骨瓣減壓術、血腫清除術和腦室外引流術。采取醫療干預措施包括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機械通氣、導尿、深靜脈置管或介入治療者239例。單用1種抗生素者157例,聯合應用2~5種抗生素者201例,并發AAD的76例患者中使用第三代頭孢菌素最多見(46例),其次碳青霉烯類(39例),克林霉素(34例),廣譜青霉素(31例),而第四代頭孢(15例)、大環內酯類(8例)、氨基糖甙類(7例)、喹諾酮類(4例)較少見。AAD患者多次糞涂片或培養為陽性球菌42例,真菌19例。
1.2 診斷標準 急性腦卒中的診斷符合1996年中華醫學會第四次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的診斷標準。本組358例急性腦卒中患者均符合上述標準。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診斷符合2001年1月2日頒發的《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的診斷標準:在應用抗生素過程中或之后新出現的腹瀉,多次糞鏡檢示球菌和桿菌比例失調,糞涂片多次發現陽性球菌或真菌,包括假膜性腸炎、出血性結腸炎、真菌性腸炎。本組76例AAD患者均符合上述標準。
1.3 方法 分析急性腦卒中患者的卒中類型、性別、年齡、基礎疾病、手術、醫療干預措施、意識障礙、聯合應用抗生素、抗生素使用時間及預后與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關系。
1.4 統計學處理 各組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
2 結果
2.1 AAD與卒中類型的關系 358例急性腦卒中患者中腦梗死組143例,并發AAD 27例(發生率18.89%);腦出血組121例,并發AAD 25例(發生率20.66%);蛛網膜下腔出血組94例,并發AAD 24例(發生率25.53%),不同卒中類型組并發AAD發生率比較,差異無顯著性(χ2=1.79,P>0.05)。見表1。表1 不同急性腦卒中類型并發AAD的比較注:*P>0.05
2.2 AAD與危險因素的關系 性別不是AAD發生的危險因素,年齡大于70歲、伴有基礎疾病、住院期間手術或采取醫療干預措施、伴有意識障礙、聯合應用抗生素、抗生素使用時間大于7天的急性腦卒中患者AAD發生率明顯增高,各組發生率比較差異均有顯著性。見表2。表2 358例急性腦卒中患者并發AAD的危險因素分析
2.3 AAD與預后的關系 急性腦卒中并發AAD組76例,其中25例死亡,死亡率為32.89%,未并發AAD組282例,其中37例死亡,死亡率為13.12%,兩組比較差異有顯著性(χ2=16.35,P<0.01)。見表3。表3 急性腦卒中并發AAD組與無AAD組死亡率的比較注:*P<0.01
3 討論
有研究顯示,急性腦卒中醫院感染部位以呼吸道最高,其次為泌尿道,第3位為胃腸道[2]。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正是醫院內源性感染在胃腸道的表現。合并糖尿病、大腦中動脈閉塞、格拉斯哥評分低于9分是缺血性卒中發生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3]。本研究顯示,急性腦卒中患者高齡,伴發基礎疾病,采取手術或醫療干預措施,伴有意識障礙,聯合應用抗生素,抗生素使用時間長,AAD的發生率明顯增高,與卒中類型、性別無關。且并發AAD組住院時間延長,死亡率高,預后差。
引起AAD的常見病原體如下:(1)難辨梭狀芽孢桿菌:是公認的引起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主要病原體,在所有AAD中占10%~25%。它可產生兩種毒素,即腸毒素A和細胞毒素B,可導致結腸黏膜損害和炎癥[4,5],臨床表現為假膜性結腸炎。(2)非難辨梭狀芽孢桿菌包括金黃色葡萄球菌、產氣莢膜桿菌、念珠菌屬、沙門菌屬,然而這些菌在AAD中的發生機制尚有爭議,因為大多數細菌被認為是腸道菌群的共生菌,而碳水化合物和膽汁酸的代謝降低也可導致AAD[6]。
國外統計資料顯示,幾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可引起腹瀉,誘發AAD,其概率大小取決于抗生素的抗菌譜、腸腔內抗菌濃度、使用劑量與療程、配伍使用等。本研究中易發生AAD的抗生素以第三代頭孢菌素為主,其次碳青霉烯類、克林霉素、廣譜青霉素,而喹諾酮類較少見。與以往文獻報道有一定差異,可能與第三代頭孢菌素、碳青霉烯類和克林霉素在本院使用廣泛有關。本研究中,發生AAD后,首先停用廣譜抗生素,若感染尚未控制就出現AAD,則換用窄譜抗生素或減量,同時服用微生態制劑以恢復腸道正常菌群如嗜酸乳酸桿菌、保加利亞乳酸桿菌、雙歧桿菌、長雙歧桿菌、嗜熱鏈球菌、酵母菌等,部分重癥病例加用甲硝唑或萬古霉素,若糞涂片或培養提示為真菌則加用氟康唑。多數病例在2~4周后好轉,少數病例感染未控制,并進一步惡化,甚至發生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而死亡。死亡原因除與AAD惡化以外,還與顱內原發疾病重,顱內感染、膿毒癥、二重感染未得到控制,或合并心、肺、腎等重要臟器功能衰竭有關。有6例復發,復發率7.9%,低于相關文獻報道[7]。
本研究中的患者住院期間由于意識障礙、長期臥床、鼻飼流質等常出現胃腸功能紊亂-便秘或腹瀉,給予導瀉劑、灌腸術及大量抗酸劑則影響了腸道正常菌群。高齡,伴有基礎疾病的急性腦卒中患者采取多種醫療干預措施及手術后機體免疫力降低,且大量廣譜抗生素的使用,在抑制致病菌的同時也抑制大量生理性細菌,使過路菌、真菌等大量繁殖而成為優勢菌,即發生腸道菌群失調,AAD的發病率隨之升高[8]。在臨床工作中我們應提高對AAD的認識,即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采取防治措施,以減少并發癥,改善預后。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顯示,我國住院患者抗生素類藥物使用率高達80%,聯合使用兩種以上抗生素的占58%,遠遠高于國外的30%。近年來我院神經ICU中AAD的發生率逐漸增高,與廣譜抗生素的廣泛應用,甚至濫用密切相關。積極采取綜合防治措施,以降低AAD的發病率尤為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合理選擇和使用抗生素,我們建議對于感染相對不嚴重的輕癥患者,盡可能選用針對性強的窄譜抗生素,避免濫用抗生素;對于急危重癥、高齡、有基礎疾病的患者根據病情需要及早選用強效廣譜抗生素,爭取盡早使感染得到控制,避免頻繁更換抗生素,并于病情好轉或感染控制后及時停藥;盡量減少預防性應用抗生素或縮短應用時間,以降低AAD的發病率;對于機體抵抗力嚴重低下者可進行消化道選擇性去污染(SDD),即預防使用消化道不吸收的較為窄譜抗生素,以預防致病菌定植,抑制需氧菌過度生長和二重感染,而不干擾原籍菌,故減少腸道菌群失調的發生,有助于降低AAD的發病率。
總之,對于急性腦卒中的患者,合理的選擇和使用抗生素,盡量減少醫療干預措施,以減少AAD的發病率,不僅可以減少患者住院時間,減輕經濟負擔,還可以改善腦卒中患者預后,降低死亡率。(參考來源:急性腦卒中并發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分析,汪皖君,中華中西醫雜志2008年第9卷第2期)
TAG:急性腦卒中并發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分析 腹瀉
相關藥品